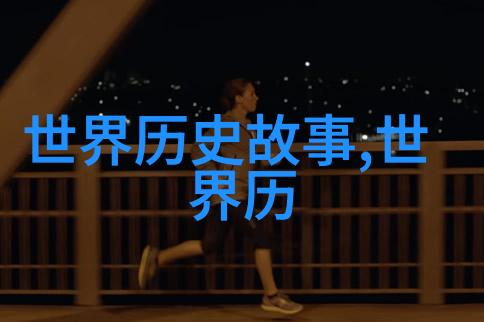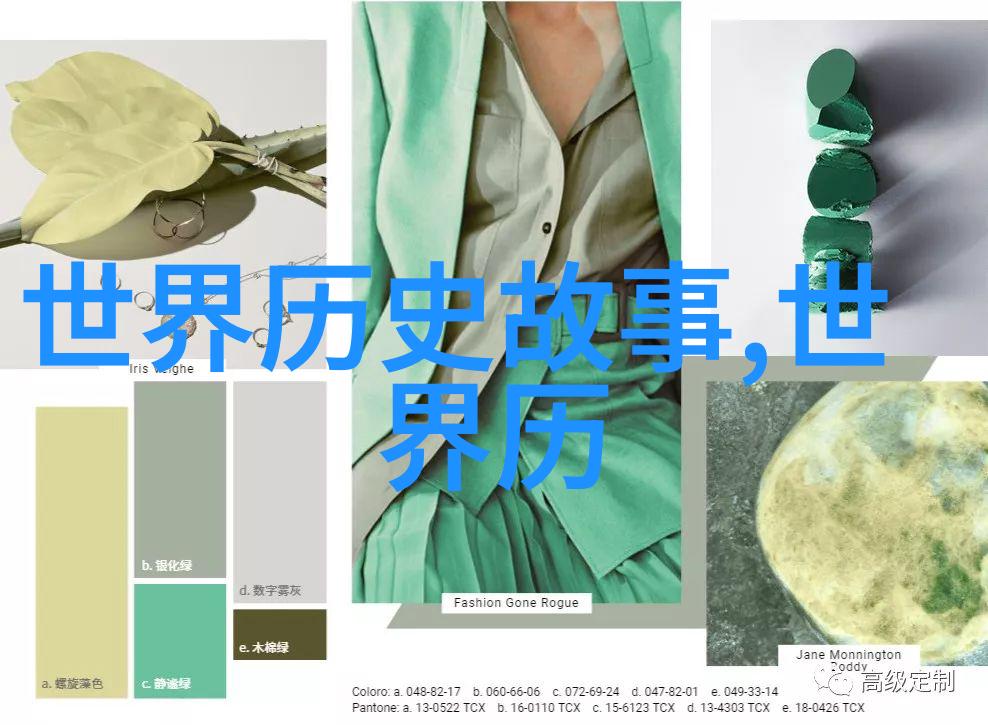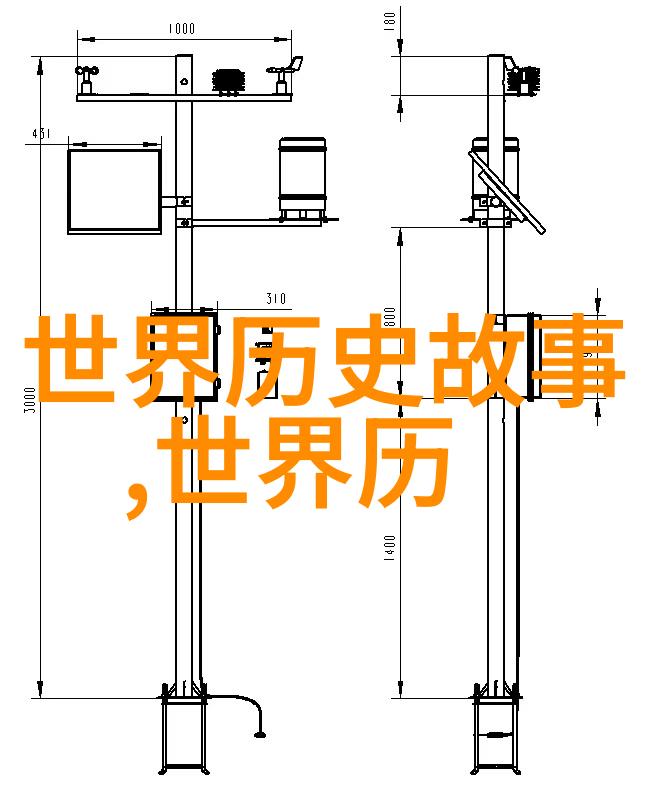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追求和谐,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心灵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和”文化深植中华文明的核心,和谐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价值观。
关于“和”的概念,诸子百家多有论述,《诗经》中多次出现“和乐”、“和鸣”的词语,《易传》中有“保合太和”的说法,《尚书》中强调“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国际环境。孔子在《论语》中说:“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主要将和纳入礼的范畴,运用规范制约达到社会和谐。墨子说:“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他以世界眼光期待四海升平。法家通过法治,主张“上下调和”。兵家、阴阳家、杂家无致力“和”文化的论述。然而,以上诸子主要是在人文社会中发掘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意义,唯有道家的和谐观念,是从宇宙和谐的高度,下落到人际和谐的过程,最终归结为天人合一的境界。
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归结出宇宙最原始的和谐,乃是混沌。《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有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在天地诞生以前就形成了,听不到它的声音看不见它的形体,它寂静而空虚,先于天地诞生,独立存在又循环运动生生不息,可以作为天地万物的总源,我不知它的名字,勉强叫它“道”。
为什么说混沌是和谐的一种呢?混沌状态,天地未分,万物未形,没有善恶、高下、贵贱等各种尺度标准,按照佛家的观点就是无分别心,无我执,万物一体,一切都是整齐划一,一团和气,也就不会有差别,无差别就不会产生纷争,没有纷争战乱,世界大同和平。所以说混沌一体才是宇宙中最大的和谐,最高级别的和谐,最原始的和谐。
老子哲学的终极目标,不是停留在那个看不见、摸不着、高不可企混沌之道上的原始和谐,而是要将原始混沌道的和谐逐渐下落到人间、人事中去,用德来表述,推广,让混沌之道变得清晰可施行、可把握、可捉摸。《道德经第二十一章》他说:“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人间大德的形态,随着道为转移。虽然道这个东西,恍恍惚惚,看起来难以捉摸,但是其中有迹象,有实物,有精质,还是可以信验的。
道是混沌不分的,大德服从道,向道学习,圆融一体,无偏无私。所以《道德经第四十九章》:“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圣人没有私心,将民心作为自己的心。百姓善良,固然善待;百姓不善良,也不摈弃,这就是得到善的表现。百姓诚实,固然信任他们,百姓不诚实,也以诚对待,这就是得到诚信的表现。圣人治理天下,收敛内心无私无欲,在圣人的治理下,百姓也浑朴无机心返璞归真,圣人像热爱孩子一般爱护百姓。
如此说来,老子貌似善恶不分,是非不辨,让人难以接受。其实,老子是构建一种兼容并蓄的伟大精神,以近乎无私无偏的大公之心,让万物各尽其性,道法自然,实现无为而治。《道德经二十七章》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天下的事物存在即是有用,不要以刻意的是非标准,格子条框它们,而造成,失衡,有违和谐。大德之人没有分别,不会遗弃任何事物任何人,只会让他们各自成长得更好,辅助万物之自然。
中国历史上,党争之祸接二连三,屡禁不止。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宋朝也不例外发生过元佑党争、庆元。公元960年,北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于陈桥驿发动,一夜间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建立宋朝,他立下一条规矩:有宋一朝不杀士大夫。然而,宋朝的读书人,也未能因此而免祸,更在不断贬谪的路上饱受侮辱。北宋中期,程颢程颐两兄弟创立后世号称的“程朱理学”。经靖康之变,南宋偏安一隅,理学传播遍及江浙,影响蔚然,成为一时显学,出现一系列大师级人物,如朱熹、吕祖谦、张栻、周必大等人。可是,当朝统治者宋孝宗排斥理学,认为清议误国,由此,无论在朝抑或在野都形成了两派,道学家与非道学家,这两派争论不断,互相打压,后愈演愈烈从学术分歧转变为事件。
话说公元1194年,宋孝宗驾崩,儿子宋光宗因不服丧被冠以不孝之名。外戚韩侂胄和皇室宗亲赵汝愚得到太后懿旨,逼迫光宗禅位给太子赵扩,是为宋宁宗。赵汝愚因拥立有功被封为右相,韩侂胄希望宁宗封他为节度使,成为一方诸侯,但遭到了赵汝愚的极力反对,由此结怨,两人嫌隙日深。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赵汝愚尊崇理学,便将朱熹召入经筵﹐为皇帝讲书。好景不长,韩侂胄运用手中权力将朱熹贬谪出京,流放至岭南山区,接着以赵汝愚的皇族身份不适合担任丞相职位为由,奏请宁宗将赵汝愚外贬永州,赵汝愚因不堪车马劳顿而病死赴任途中。此时,一批正义官员不满韩侂胄行为,纷纷为赵汝愚鸣冤,韩侂胄将他们统统划分为道学一派,进行打击贬谪。凡与他意见不合的士大夫都被称为“道学之人”,又斥道学为“伪学”。凡科举考试中,文章涉及义理的士子,一律不予录取,儒家的四书五经更是为当朝。不久,宋宁宗又下诏,订立“伪学逆党清单”,名列党清单中的人都受到了压制排挤贬谪,乃至致死的惩罚,凡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也都受到牵连,不许担任官职或参加科举考试。
“伪学逆党清单”的出炉,标志着庆元的巅峰。巅峰之下,必是滑坡。公元1200年,理学大师朱熹在福建逝世。一个当时的学界宗师之葬礼却平淡无奇,几乎没有民众去吊唁,只有朱熹的几位忠实的学生简朴地将他埋葬了。朱熹死后两年,历时六年的“庆元”才彻底结束。国家的悲剧在于它因言废人,让光芒闪耀的巨星掩埋尘埃。人间是非皆由人定,当权者囿于己见,借题发挥排除异己,学术争论沦落为的杀人工具,这是历史的一种。
1957年,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分子进攻的指示》标志着反斗争在全国开始。指示声称:“资产阶级分子,是、反人民、主义分子,虽然我们把他们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实质上,他们同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一种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点,必须明确,必须清醒。”由于中央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把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少数等55万人错划为“分子”。在文化大期间,许多分子饱受折磨,饱经人格侮辱,落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浩劫,大恶难书,让人不寒而栗。人士章伯钧先生说:“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遵守精神,确立的作风,尊重异己,接受批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
庄子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又说“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所谓,真理没有确理,言论没有定准,是非、对错、曲直没有标杆,儒墨各自以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才是正确的,这样才形成各种差别、界限、争论。人间社会犹如罗网,人心沉溺自我,彼此的争端中不能自拔,造成心灵的自闭,违背精神的自由和谐。只有以开放的心灵,打破以自我为中心的层层界限,包涵万有,平等齐物,与道通于一,才能实现身心的大和谐。
责编:紫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