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的著名故事农村的起飞接近发达国家的脚步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七十年前,萧红在她的成名作《生死场》里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一语成谶。按说,七十年来,东北乡村的生活早已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人也换了一代又一代,但当打开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的时候,第一个冲进脑子里的感受还是这句话。当然,这一次生和死的“忙”,早已不是当年为了抵抗日本,为了反抗夫权父权的“忙”,而是另一番决绝和挣扎的景象。在这景象里,不再是古老的小屋,而是新建的大房子;不再是手工制作的手灯,而是路灯;不再是一片荒凉,更是一片繁华。
然而,在这里晃动的是人们,他们的心情却未能完全融入这一切带给他们幸福的一刻。他们还保持着“灰头土脸”的旧模样。这本书出版方定位为长篇小说,却像是一个乡村访谈录。在书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与几个精神医学学生对农村遗族进行调查采访。“农村”加上“遗族”,让我们预感到这是一个悲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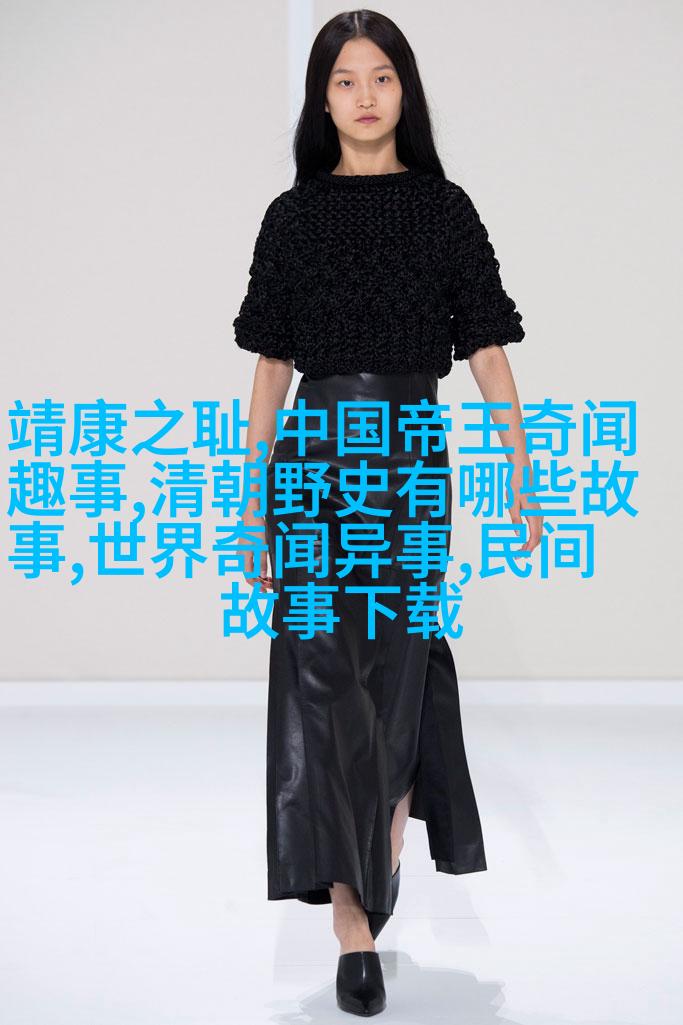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卑微者更应强韧,但外界压力让他们变成了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承受最深重苦难,同时也承载最浓烈希望,他们奋斗、翻盘、励志,是正能量。但当这个故事揭开乡村角落时,一切被修正了。
这些故事并非用来揭幕,而是在新闻报道中,它们更令人震惊、难以置信。如果不是集中呈现,每个故事单独拿出来,都会变成滔滔新闻中的渺小事迹——隆隆向前的社会车轮碾压个把人,无论何时,只要历史进步,便有普通人的血迹推动它前行,或许这是贡献的一种形式。

每个人都是同一个问题之下的具体案例,有相同功能,却不值得追究差异性;背后暗含社会学心理学共性则值得探讨。《生死十日谈》是一本发现提醒之书,是写给启蒙者研究者决策者的书。
生的卑微、死草率,《生死十日谈》讲述的是“死”的故事,大多数沉郁压抑,以善良愚昧质朴无知可怜可恨形容的人物。大多数处理生命如鸡猪一样鲁莽草率,对生命基本价值尚且无知,更遑论尊严了。

伴随死亡草率必然有生的苦痛。这本书透过生的寥落破败依稀见到忍耐爱坚持。而最后一个关于大辫子的爱情故事,让读者感受到温热之处,即便如此,“小老头”去世,大辫子的人生才算真正被唤醒,她懂事儿了...
此外,在宗教或类宗教寻求解释的情感依托,从另一个世界获得消息,也成为他们救赎之路。而参与调查的心理学研究学生们只能倾听流泪支付误工费。这就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著名故事:农村从低谷崛起,其发展速度几乎赶上了某些发达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