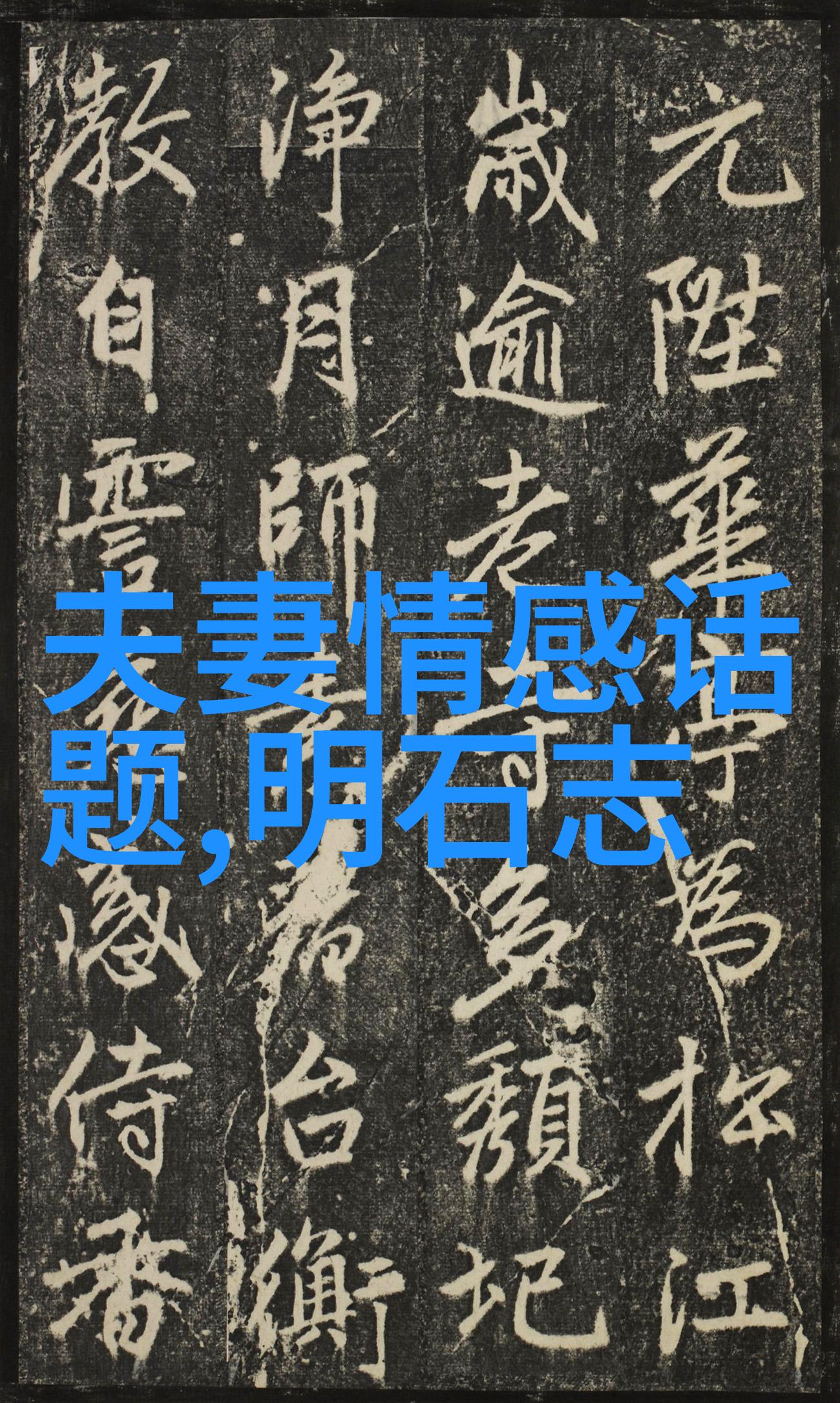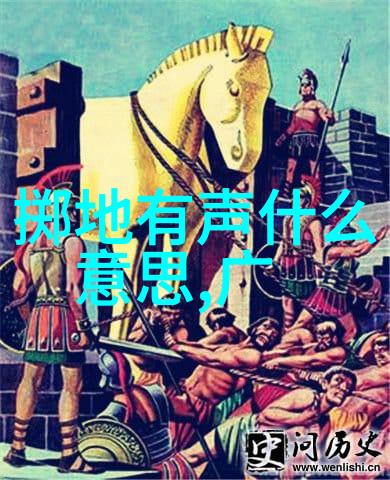中国农村发展奇迹从落后到赶超率近发达国家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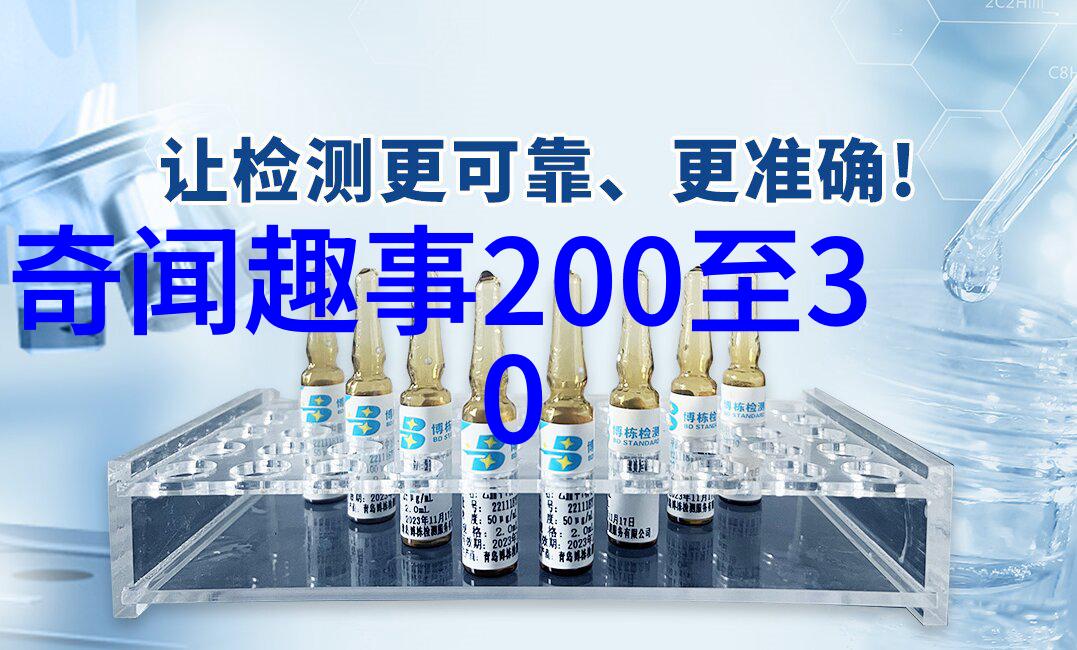
七十年前,萧红在她的成名作《生死场》里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没有想过自己可以一语成谶。按说,七十年来,东北乡村的生活早已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变化,但当打开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的时候,第一个冲进脑子里的感受还是这句话。当然,这一次生和死的“忙”,早已不是当年为了抵抗日本、为了反抗夫权父权的“忙”,而是另一番决绝和挣扎的景象。在这景象里,大片大片被种植的小麦与高粱,如同金色的海洋,在阳光下闪耀;太阳能热水器顶上,有时会冒出几缕白烟,让人联想到遥远的地方,还有更多未知的事情等待发现。
然而,在这里晃动的人影,却远未感受到这一切带给他们的幸福,或许,他们的心灵并未脱去“灰头土脸”的旧模样而与之匹配。这本书出版方的定位是长篇小说,但给人的阅读感觉却更像是一本乡村访谈录。书中收录的是作者夫妇和几个精神医学和应用心理学学生对农村遗族调查采访。“农村”+“遗族”,这样的关键词一出,便可想而知了——这是一个卑微者还要悲惨世界。

一直以来,我们文化基因里都认为卑微者的生命理当更强韧,而外部世界加给他们的一切,只能让他们变成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承受最深重苦难同时又承载最浓烈希望,他们是奋斗者,是命运翻盘者,是励志者,是正能量。但当这本书静悄悄揭开乡村世界角落的时候,一切都被修正了。
每个故事,都像是社会车轮碾压个把人的缩影,或许隆隆向前的历史车轮,也不过是在普通人的血迹上行驶。而这些普通人的血迹,被视为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一种贡献,从这个角度看,《生死十日谈》也是一本发现提醒之书,是写给启蒙者、研究者以及决策者的书。

生的卑微,与死草率相伴。在这些故事中,每个人裁决自己生命时,都似乎没有经过清醒理性的选择与斟酌,他们处理自己就像处置鸡猪一样鲁莽草率。即便如此,对于这些卑微者的社会环境,又或许也是无情漠然,没有将其视为尘埃草芥。而对于生命基本价值尚且无知,更不用说生命尊严了。
伴随着死亡草率,不得不面对的是生的苦痛。通过生的寥落破败,我们依稀能够看到人性忍耐爱坚持。这,也总算让我们在冰冷一片“死”中感受到温热的一个点,即使那只是极小的一个点。大辫子的故事,就像是全书写得最好的一个,它展现了一份爱,那份爱跨越了世俗所谓的情感界限,将艺术呵护至终老,而那个男主角则以身殉情意,使得整个故事充满了一抹温暖色彩,最终唤醒了大辫子的人生,让她懂事儿起来...

此外,这些故事中宗教或者类宗教出现频繁,它们成了那些迷茫中的寻求依托解释需要来自另一个世界消息的地方。不论是一个倾诉、一次辩白、一次暗示,都可能成为它们救赎之路。而参与调查研究生的专业知识,却如同空气般渺不可闻,只剩下倾听、流泪,以及支付40元误工费作为回报。这一切,无疑又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于我们的探索之旅...